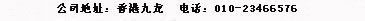惡性胸腺腫瘤延誤診斷案談醫療民事訴訟
月旦醫事法報告 年12月號
惡性胸腺腫瘤延誤診斷案
談醫療民事訴訟舉證責任
之減輕與轉換
王旋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法官
事實概要
原告於年7月25日因腹痛伴有發燒現象,前往乙醫院急診處就診,於接受胸部X光檢查後,該院醫師發現其胸部縱膈(mediastinum)及肺門(hilum)處有明顯腫塊陰影,另於肋膜上也有多處腫塊,經住院接受電腦斷層影像檢查後顯示「左胸肋腔有多發性結節與腫塊,最大之腫瘤位於左側胸腔上部,有7×6×8.3公分大小、左側胸肋膜積水、主氣管旁有多發性淋巴結腫大,最大達到1.4公分,另在右腸繫膜接近迴盲瓣區域之有多發性小淋巴結」,嗣後就腫瘤為穿刺切片檢查,確認為惡性胸腺瘤(malignanthymoma)。原告於乙醫院住院期間,調閱其前於年9月12日在甲醫院接受健康檢查拍攝之胸部X光片供乙醫院醫師參考,經該院醫師檢視發現健檢當時已可見原告胸部之腫瘤,惟甲醫院核發之檢查報告,關於胸部X光部分之結論為正常。原告主張為其健檢X光片進行判讀之放射科專科醫師A、總結檢查結果後負責核發健檢報告之醫師B,就X光片之判讀有疏失,並對A、B醫師及甲醫院提起訴訟請求損害賠償(下稱健檢胸部X光誤判正常案)。
判決摘要
一、原告主張
依原告於年9月12日在甲醫院健檢時拍攝之X光片影像,其胸部之腫瘤於斯時已明顯可見,X光片顯示之結果不應判讀為正常,且原告當時僅於縱膈腔部位有初發病灶,左肺並無任何變化,故此縱膈腔腫瘤應屬初期,若能及時診斷,並不需要進行化學治療,只要直接作小範圍之腫瘤切除即可,5年存活率尚高達90%。原告因A、B醫師健檢X光片之判讀有疏失,無法即時進一步接受關於胸部之診斷及治療,直到年7月25日在乙醫院發現腫瘤並接受治療時,已是臨床分類第四期,致原告病情已經擴大至必須先接受化學治療,再為廣泛範圍之手術,且生存機會驟降,5年存活率降到不及25%,故原告受有至少喪失5年存活率65%之損害,而屬人格權之侵害,其因此所受財產上損害為:含美國醫院進行手術及化學治療之費用、生存機會喪失所減少勞動能力等,並請求精神慰撫金。
二、被吿答辯
(一)原告至甲醫院診所接受健康檢查,僅與甲醫院間成立健康檢查之契約關係,並非醫療行為。且健康檢查本非精密診療,X光拍攝之精細度無法與超音波、斷層掃瞄相比,甲醫院已告知「此次健康檢查結果數值在正常範圍,並不全然代表身體沒有潛在疾病」並提醒原告對自己身體變化警訊應及早就醫。
(二)A醫師判讀健檢X光片時,因X光片僅能勉強顯示原告胸部正面第9根肋骨,加以並無側面X光片,原告亦無臨床症狀,其理學及血液檢查復未有任何異常,因而認該X光片屬原告吸氣不足,應係縱膈腔內心臟血管擴大鼓起所形成之陰影,乃依當時所得資料判讀該X光片為正常,自無判讀上之任何疏失。
(三)況僅以胸部X光根本無法直接判斷是否係縱膈腔異常,亦無法判斷原告當時是否罹患惡性胸腺瘤,而必須仰賴手術及病理切片,始能確認惡性胸腺瘤侵犯之範圍及期數。
(四)惡性胸腺瘤之形成並非取決於時間之長短,亦不因時間延長致加重惡化。至生存機會(即存活率)應依腫瘤形成時有無侵入性,及如屬侵入性其侵犯範圍之不同而予區別,尚與時間之長短無關。原告經乙醫院檢查為惡性胸腺瘤,僅得認其腫瘤形成時屬侵入性腫瘤,並散布到肋膜或心包膜範圍,尚不足據以推論原告於接受健康檢查時必定已罹患惡性胸腺瘤第一期,並因健檢X光片判讀錯誤而拖延至乙醫院檢查時發現已成為第四期。
(五)再者,健檢報告雖由B醫師出具,然健檢X光片之負責判讀醫師為A醫師,B就該X光片僅需以放射科專科醫師即A醫師之判讀為基礎,並綜合各科別專責醫師所得各項資料後出具報告,並無就X光片重複判讀之責任。是原告主張B醫師判讀X光片亦有過失,應非正確。
三、重要醫事證據
(一)馬偕紀念醫院年8月22日馬院醫內字第號函檢附鑑定報告(下稱第一次鑑定回函):
1.病人於年9月12日之胸部X光片,在主動脈弓及主動脈肺動脈窗附近,有疑似異常。上述異常,無法直接判斷是否為縱膈腔之異常。
2.上述之異常可能情形有:肺癌及縱膈腔腫瘤(如淋巴瘤、胸腺腫瘤、畸胎瘤等),其「僅係心臟附近血管所造成之陰影」,可能性不高。並無法排除「胸腺瘤初發病灶所造成之陰影」。
3.依臨床醫學實務,吸氣不足確實容易導致心臟附近血管較為鼓起。病人接受胸部X光檢查時無吸氣不足之情形。
4.如果醫師判讀X光片認為有異常,若是因為攝影時的條件不佳,必須考慮重拍,若攝影條件良好,則一般可以比較與舊片之差別來增加判斷依據,或安排電腦斷層以獲得更多影像資訊。
5.本件健檢判斷原告胸部或腫瘤檢查為正常之結果,並不正確,不符合當時臨床醫療水準。
6.上開X光片,其曝光、X光強弱、清晰度、病人呼氣程度等拍攝條件,足以作為判讀胸部X光之用。
7.依據目前醫學知識,惡性胸腺瘤之病程演進根據Masaoka分期系統可區分為四期,第一期至第四期之5年存活率分別為96%、86%、69%、50%。
8.而病人於年7月25日至同年月31日於乙醫院接受檢查時之病程期數,根據電腦斷層結果,其臨床分類為第四期。
9.依照目前醫學知識及儀器設備,無從以病人事後在乙醫院之檢查結果,推估其所罹患惡性胸腺瘤年9月12日接受健康檢查時之病程期數。
(二)馬偕紀念醫院年10月28日馬院醫內字第號函(下稱第二次鑑定回函):
1.健檢X光片吸氣充足,確可判讀受X光檢查者之吸氣充足。
2.該陰影於醫學解釋判讀上,不能完全排除心臟附近血管鼓起所造成之陰影之可能性,而仰賴胸部電腦斷層進一步判斷。
3.惡性胸腺瘤疾病之形成原因不明。……於醫學上並非以瘤的大小作為分類,……WHO……並無特別說明是否循序由A演變為AB、B1、B2、B3及C之期型,或是自始至終為單一細胞型態,此細胞型態必須在手術病理切片後判定。WHO……此分類法中,罹患此疾病之某一類型者,因時間之延後加長而演變成為另一類型,目前並無明確文獻證據。
四、判決理由
(一)健康檢查所為之診察、診斷行為,屬醫療行為。
(二)針對A、B醫師所為醫療行為,有無注意義務違反之說明:
1.A醫師之醫療行為,有注意義務之違反:
歷審判決均認A醫師有注意義務之違反,理由略以:依據馬偕醫院第一次鑑定回函,健檢X光片檢查結果在病人主動脈弓及主動脈肺動脈窗附近,有疑似異常現象,身為放射專科醫師之A於判讀後卻為正常之判斷,不符當時之臨床醫療水準,自屬於診斷之醫療行為,未能善盡其醫療職務上應具備之注意義務,而為有過失。
2.針對B醫師之醫療行為,有無注意義務違反:
(1)臺北地方法院判決認B醫師亦「有」注意義務之違反。
A醫師判讀健檢X光片為正常之結果,並不正確,不符合當時臨床醫療水準,此業據馬偕醫院鑑定明確,B醫師亦怠於查證、確認,即遽援引作為檢查報告內容之一部,自屬有過失。又B醫師之經歷為兒科主治醫師,固非放射科專科醫師,惟將X光片判讀為正常,既不符合當時之臨床醫療水準,此醫療水準不應因判讀醫師所屬專科為放射科或兒科而有所差異。
(2)在該案上訴至臺灣高等法院時,臺灣高等法院即基於下列理由,認B醫師「無」注意義務之違反:
B雖為甲醫院核發健檢報告之醫師,惟醫院之各科醫師本各有專精,殊難要求核發檢查報告之醫師須精通所有科別,而具備就健康檢查所得之各科資料均得逐一進行判讀之能力,且經其逐一判讀無訛後,始得核發檢查報告。是依常情最後出具檢查報告之醫師,應僅係參照各科專責醫師所判讀之結果,整理比對綜合結論後,據以核發檢查報告。是B醫師係小兒科醫師,非放射科醫師,又其復無再就健檢X光片重複判讀之義務,則其依據A醫師判讀結果為基礎出具健檢報告,難認有注意義務之違反(此結論為最高法院年度台上字第號判決所採,故原告對B醫師之損害賠償請求自此即遭駁回確定)。
(三)惟A醫師注意義務違反,與原告年7月25日就診發現罹患惡性胸腺瘤第四期,致受有未及時就醫、存活率驟降之損害間之因果關係,有認應依民事訴訟法第條但書規定,由被吿就「不」具因果關係一節負舉證責任,亦有認應由原告就存在相當因果關係一節負舉證責任。
1.認應由被吿就不具因果關係一節負舉證責任(臺北地方法院99年度醫字第66號判決)
(1)適用民事訴訟法第條但書之理由
原告並非具醫學知識之人,被吿則為專業醫院及醫師,故就提出相關醫學文獻佐證,或聲請法院囑託有醫療專業知識之人或機關進行鑑定事項及詢問,被吿顯然較原告具有優勢,而容易取得及提出證明方法,是應適用民事訴訟法第條但書規定,轉由被吿就不具因果關係一節負舉證責任。
(2)因果關係之判斷
i.依原告於乙醫院檢查經過,其發現罹患惡性胸腺瘤,除接受X光檢查外,尚需經電腦斷層影像檢查及腫瘤穿刺切片檢查,依健檢X光片無法直接判斷原告是否縱膈腔異常,且依照目前醫療知識及儀器設備,亦無法從事後原告於乙醫院之檢查結果,推估原告於健檢時之病程期數,依此,被吿辯稱健檢X光片並不足以直接判斷原告胸部是否縱膈腔異常或已罹患惡性胸腺瘤,尚非無據。
ii.惟依馬偕醫院之鑑定,健檢X光片已有異常狀況,且無法排除為胸腺瘤初發病灶所造成之陰影,被吿未能舉證證明前開X光片異常並「非」胸腺瘤初發病灶所造成之陰影,復未能舉證原告於年間為其健檢時,並「未」罹患惡性胸腺瘤,或者縱已罹患惡性胸腺瘤但其期數並未早於其於乙醫院發現時之期數,堪認A醫師之過失,與原告存活率降低之損害結果間具有因果關係。
2.認應由原告舉證相當因果關係(臺灣高等法院年度醫上字第6號判決)
(1)因果關係之判斷
i.原告於美國醫院就診之記錄可知,其除罹患第四期之惡性胸腺瘤外,實際有多個病灶,尚有局部淋巴血管侵入之B2型胸腺瘤及四個未含有癌細胞之淋巴結。且依馬偕醫院第二次鑑定回函表示「該陰影(即X光片異常陰影)於醫學解釋判讀上,不能完全排除『心臟附近血管鼓起所造成之陰影』之可能性」,可見健檢X光片異常現象,並不當然證明原告斯時已罹患惡性胸腺瘤,亦有可能係美國醫院手術中發現其罹患之淋巴瘤、B2型胸腺瘤,甚至可能僅係單純心臟附近血管鼓起所造成之陰影。
ii.又馬偕醫院第一次鑑定回函說明,依照目前醫學知識及儀器設備,無從依病人在乙醫院之檢查結果,推估其所罹患惡性胸腺瘤於年9月12日接受健檢時之病程期數。第二次鑑定回函更詳盡說明:惡性胸腺瘤疾病之形成原因不明。……於醫學上並非以瘤的大小作為分類,……WHO……並無特別說明是否循序由A演變為AB、B1、B2、B3及C之期型,或是自始至終為單一細胞型態,此細胞型態必須在手術病理切片後判定。WHO……此分類法中,罹患此疾病之某一類型者,因時間之延後加長而演變成為另一類型,目前並無明確文獻證據。是依馬偕醫院前開鑑定回函可知,依目前醫學知識及儀器設備,無從推斷其於健檢時已罹患惡性胸腺瘤,且胸腺瘤之分類非以瘤的大小為基準,亦非循序由A逐漸演變為C型之惡性胸腺瘤,亦不因時間之延後加長而演變成為另一類型,是縱原告於乙醫院檢查發現罹患惡性胸腺瘤,亦無從推估其於健康檢查時之病程期數為何,是尚難認A醫師就健檢X光片判讀錯誤與原告事後罹患惡性胸腺瘤且病程進化為第四期之結果,具有相當因果關係。
(2)不適用民事訴訟法第條但書之理由
原告年9月12日健康檢查時尚未罹患惡性胸腺瘤一節為消極事實,且依目前醫學知識及儀器設備,尚無從推斷其於健檢時是否已罹患惡性胸腺瘤,此外,胸腺瘤之分類亦非循序由A逐漸演變為C型,更不因時間之延長而演變為另一種類型,此均據馬偕醫院鑑定回函明確。且原告於年7月間前往乙醫院檢查發現罹患第四期惡性胸腺瘤之時間距離年9月12日健檢時間,已相隔近兩年,該兩年期間原告身體變數極大,如苛責健康檢查判讀之醫師須就兩年前之病人身體狀況「未」罹某病症之消極事實負舉證責任,顯失公平,故認仍應由原告就健檢時A醫師就X光片判讀錯誤,與其事後罹患第四期惡性胸腺瘤之結果間有相當因果關係一節,負舉證之責。
3.認應減輕原告關於相當因果關係之舉證責任(臺灣高等法院年度醫上更(一)字第5號判決)
(1)適用民事訴訟法第條但書之理由
同臺北地院99年度醫字第66號判決,惟適用民事訴訟法第條但書之結果,係減輕原告關於因果關係之舉證責任,而非轉換舉證責任。
(2)因果關係之判斷
i.A醫師對X光片之檢查有判讀錯誤,若非A醫師之醫療過失,原告必然會及早進一步治療,不至於遲至年間始在乙醫院檢查出惡性胸腺瘤之結果,故A醫師之醫療過失,與原告未能及早發現延誤就醫致病程演進至第四期惡性胸腺瘤之結果,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原告已盡減輕後之舉證責任)。
ii.A、B為醫事專門人員、甲醫院則為醫療機構,均具有醫療專業知識上之優勢,卻未能就原告於年9月12日接受健康檢查時,並「未」罹患惡性胸腺瘤,或縱已罹患惡性胸腺瘤但期數「未」早於乙醫院檢查時之期數及兩者間不具因果關係提出相關事證證明,其空言否認,應屬無據(A、B、甲復未能提出反證)。
4.最高法院關於本案因果關係之看法
最高法院於第一次發回時,並未就因果關係之舉證責任應由何人負擔、或是否應減輕舉證責任各節為說明,而係以:倘原告之腫瘤於年間健檢至年間至乙醫院診療期間並無變化,以腫瘤之大小(最大腫瘤位於左側胸腔上部,有7×6×8.3分大小),健檢X光檢查應無未顯示之理,能否認原告之舉證,不足證明其腫瘤於該段時間確實惡化,A醫師對X光片判讀錯誤,與原告未能及時追蹤治療致罹患第四期惡性胸腺瘤之結果間,無相當因果關係,尚有疑義一情,為發回之理由。至最高法院上訴駁回之判決,僅說明更審判決之認定經核於法並無違誤,而為駁回上訴之理由。
判決評析:論舉證責任之減輕與轉換
一、民事訴訟之舉證責任
按臺灣民事訴訟之舉證責任,係規定於民事訴訟法第條:「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依前揭條文之意旨,如欲求有利於己之判決者,應先為有利於己事實之主張(即學說所指之「主張責任」),再就前開事實為舉證(即學說所指之「舉證責任」)。而所謂「有利於己之事實」仍有過於抽象、缺乏標準可循之質疑,德國證據法權威Rosenberg基於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若無一定法條之適用,則無法獲得訴訟上請求成果,即失其意義,因而提出「法律要件分類說」或「規範說」,以民法為基礎將法規範進行分類,由主張權利之人,就權利發生之法律要件存在之事實為舉證;否認權利存在之人,應就權利妨害法律要件、權利消滅法律要件、權利受制法律要件負舉證責任。又訴訟上當事人依循前開規則就有利於已之事實為舉證,即所謂「主觀舉證責任」,惟在兩造當事人於案件審理中已踐行應負之主觀舉證責任後,仍有事實真偽不明之情形,法院應分配由何一當事人承擔此事實真偽不明之不利益,此即所謂「客觀舉證責任」。
二、醫療訴訟之舉證責任
在醫療訴訟,原告對醫師或醫院起訴請求損害賠償,通常係依侵權行為責任及契約責任之不完全給付為請求權基礎,並請求擇一為勝訴判決,依據前揭「法律要件分類說」或「規範說」所揭示舉證責任分配原則,應由提起訴訟之原告就侵權行為及不完全給付之權利發生要件事實為舉證。以比較法之觀點,德國醫療之民事責任,被害人請求損害賠償亦係以契約責任或侵權責任為依據,並由被害人就醫療之瑕疵、醫師或醫院或其履行輔助人之過失、醫療瑕疵與損害之因果關係等三項構成要件,負舉證責任,而與前述臺灣關於醫療訴訟舉證責任之負擔一致,其考量為:病人原則上應就其請求負舉證責任,意味著醫師僅應就違反醫療義務之行為負責,並因而確保其專業活動自由。反之,倘若病人一旦因醫療而受損害時,法律立即課予醫師應就其醫療行為之無瑕疵負舉證責任者,則醫師於採取醫療行為時,將無法一直向前看(nachvornschauen),而係凡事優先考慮自保措施,準此,由病人就醫療瑕疵負舉證責任,亦有助於避免防禦性醫療行為之發生。
惟病人通常不具醫療專業知識,相較於醫院或醫師,處於資訊絕對不對稱之劣勢地位,學者亦有以在醫療訴訟中主張權利之原告,於主張及舉證上將面臨:(一)事實上不知;(二)專業上不知;(三)證據之偏在等種種困境,故在醫療訴訟進行中,宜為合理分配醫病間舉證責任,以符合訴訟上武器平等之要求,即得適用年增設民事訴訟法第條但書規定「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而例外承認不受「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此原則規定之拘束,使位居舉證能力劣勢者,回歸與對造當事人處於訴訟遂行上平等之地位,而謀求兩造間公平。此參以司法院關於民事訴訟法第條但書規定之提案理由:「民事舉證責任之分配情形繁雜,僅設原則性之概括規定,未能解決一切舉證責任之分配問題,為因應傳統型及現代型之訴訟型態,尤以公害訴訟、交通事故、商品製造人責任及醫療糾紛等事件之處理,如嚴守本條所定之原則,難免產生不公平之結果,使被害人無從獲得應有之救濟,有違正義原則」,即可明白醫療訴訟中有適用民事訴訟法第條但書調整舉證責任,以維護兩造當事人訴訟上平等地位之需求。以下分別說明民事訴訟法第條但書於醫療訴訟主、客觀舉證責任之意義:
(一)醫療訴訟之主觀舉證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條但書規定「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以達成當事人間訴訟上武器平等原則為目的之觀點,並非僅有轉換舉證責任一途,舉證責任之轉換,無疑屬最強烈之手段,其他較為緩和之方式,尚有降低原告所負舉證責任具體化之義務(容許原告僅大略陳述何項醫療行為其認為有疏失,以及何項損害是基於該行為而生)、強化不負舉證責任之當事人之事證蒐集協力義務(如命他造應就舉證人關於應證事實有關之文書及其內容之查詢在一定期間內答覆)。實際在醫療訴訟之審理過程中,法院先依原告所主張瑕疵醫療行為之事實,命被吿說明治療經過並指出相關病歷資料,並依民事訴訟法第之1條規定將審理過程分為爭點整理及調查證據階段,據被吿提出相關病歷資料整理兩造不爭執事項,再針對兩造之爭點集中調查證據。故醫療訴訟之審理在法官為訴訟指揮時,適度降低原告具體化陳述之義務、並加強被告事證提出與蒐集之協力義務情形下,已相當程度落實兩造武器平等原則之要求,醫療訴訟主觀舉證責任之界線亦因此趨於模糊,此似即為學者所謂「主觀舉證責任理論在加強法官訴訟指揮權之情形下,已失其意義」。
(二)醫療訴訟之客觀舉證責任
惟如針對原告主張之權利要件發生事實,在法院已窮盡一切可能的、訴訟上允許的證據方法,仍無法獲得確信,如何依民事訴訟法第條但書規定調整客觀舉證責任,將此事實真偽不明之不利益分配由一造當事人承擔,以符合當事人間之公平,此即為本文所欲討論之重點。
依最高法院年度台上字第號裁判意旨:「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責任,民事訴訟法第條前段定有明文,此即舉證責任之分配原則。但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如遇有特殊情形,仍貫徹此一原則,對於該當事人顯失公平時,即不受此原則規定之限制,此為該條但書『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之立法意旨。是以,倘有該條但書所定,依其情形顯失公平之情事,僅不受上述舉證責任分配原則之限制而已。亦即於斯時該當事人之舉證責任,究應減輕或予以免除?或轉換由他方當事人為之?法院應本於誠實信用原則,斟酌各種具體客觀情事後,以為認定。非謂因此得將舉證責任一概轉換予否認其事實之他方當事人負擔,始符公平正義之本旨」。是究何種情形可認符合民事訴訟法第條但書規定之「顯失公平」?又縱符合顯失公平之要件,則應發生減輕或轉換舉證責任之法律效果,仍有賴法院於個案審理中為法之續造。又法院於個案審理中關於舉證責任調整,有學者認應為事件類型之思考,即考量個案之類型隸屬,是否具有危險領域理論、武器平等原則、誠信原則、蓋然性理論等所強調之舉證責任調整必要性之特徵,而不可恣意於相同事件類型,卻於不同個案因基於直覺、感性(同情)等非理性因素或理由不足之論據,而任為舉證責任之調整,以致造成實體法原已設定之價值體系及法律安定性遭破壞,並造成人民於舉證責任法則之客觀性與平等性,以及可預見性喪失期待,此誠為的論,殊值認同。
是審判實務上之舉證責任調整之操作,應平衡追求「避免防禦性醫療行為之發生」、「醫病間資訊之絕對不對稱」及「避免法律安定性遭破壞」等價值,或參考外國立法例之借鏡。如未謹慎操作而在遇事實真偽不明之情形下,逕為舉證責任之減輕或轉換,將不利於醫病關係之長遠發展。
三、德國實務之借鏡
德國實務上為平衡病人與醫師在醫療訴訟上的平等地位,於下列幾種例外情形為病人舉證責任之減輕或轉換:
(一)表見證明之運用
透過生活經驗證明過相同形式的過程,而存在有所謂的「典型的事件過程」(依據經驗法則,有特定之事實,即發生特定典型結果者),透過此種事件過程的典型性,使病人不必再對該過程中某個事實上個別狀態進行證明。表見證明適用的前提即係存在有所謂的「典型的事件過程」,在出現某特定結果時,法官在不排除其他可能性的情形下,即得推論有該特定事實存在。例如醫師手術,將鑷子或棉布遺留在體內,就可以認定醫師或醫院手術有過失而遺留於病人體內。此時,被告應舉證尚有其他「非典型事由」可能導致相同結果,以動搖法院之推論,而再度要求病人舉證,否則,法院得基於自由心證認定該手術工具係屬於醫療人員之過失而遺留於病人體內。
表見證明原則係依據經驗法則所整理形成之「典型事件過程」,惟基於人類身體組織之複雜性,及治療條件與治療過程之多樣化與變化性,故在醫療之經驗法則上,因病人出現特定結果,而當然可以推論該結果與醫師之治療有關之情形,並不多見。
(二)重大醫療瑕疵的發生
醫師在診斷或治療上有重大疏失時,病人就損害與醫療疏失間之因果關係的舉證責任,即發生轉換之效果。關於醫療瑕疵或醫療錯誤是否「重大」,係根據一般客觀之醫師觀點,依照通常醫師所受之教育及醫學知識,該醫療瑕疵之發生,是不可理解的,而看來損害結果應由醫師負責,因為該醫療瑕疵不該發生在醫師身上,且該醫療瑕疵通常適足以造成損害之發生,於此情形下,則由被告負擔結果與醫療瑕疵間無因果關係之舉證責任。實務上的案例包括:未診斷出病人小腿有栓塞、未注意病人敗血症之症狀,而診斷為關節炎等。
又重大瑕疵原則,並非以懲罰醫師之重大醫療過失為目的,從而,判斷醫師有無重大醫療瑕疵時,並不斟酌個案醫師之主觀可非難性,且重大瑕疵之認定,亦不以醫師有重大過失為必要。
(三)可完全控制之危險原則
如果醫療行為中之危險係完全來自於醫師或醫院,可由醫院或其人員完全予以控制(如病人於股關節手術時,施行全身麻醉,卻因連接橡皮管脫落,而產生缺氧,致使腦部嚴重受損。或例如病人於輸液時因所輸溶液遭到細菌污染而發生敗血症),而與人體組織之差異性無關時,則不論是契約上或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於損害結果發生時,均應由醫師就其已盡相當注意義務以控制危險,避免損害結果之發生,從而無過失或不具因果關係,負舉證責任。
(四)病歷記載義務之違反
醫師有詳細記載病人病情於病歷上之義務,如醫師違反規定而漏未記載,且該漏未記載足以顯示出有重大醫療瑕疵,病人因而難以舉證時,即發生舉證責任轉換之效果。
(五)告知或說明義務之違反
醫師或醫院對病人的診治有告知或說明義務,其是否已向病人告知或說明病情,並得其同意而為診療行為,一旦有爭執,應轉換由醫師負舉證責任。
以德國醫療訴訟之審判實務而言,上開各原則中,重大瑕疵原則之適用為舉證責任最主要之案例類型。且由前開介紹德國法醫療訴訟之舉證責任可知,是否為舉證責任之調整,應考量個案之特殊性,並就個別之待證事實為判定。
四、醫療訴訟中客觀舉證責任分配之實務見解
在民事訴訟法第條於年間增設但書規定後,最高法院年度台上字第號裁判意旨謂:「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條定有明文。依前開規定,並無醫院或醫師應就其醫療行為先負無侵權行為舉證責任之情形,如由主張醫院或醫師有過失者,先負舉證之責,尚無違反上開規定或有顯失公平之情形,則上訴人主張本件應由被上訴人先就其醫療行為並無侵權行為負舉證之責,顯係就消極事實先負舉證責任,違反前述舉證責任之規定,自應由上訴人先就被上訴人有過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即未將民事訴訟法第條但書規定納入舉證責任分配之考量。嗣最高法院晚近見解陸續針對調整舉證責任所可採用之減輕或轉換舉證責任,於個案之具體適用提出看法,茲舉數則案例如下:
(一)「減輕」舉證責任
1.腎臟手術致十二指腸破裂案
最高法院年度台上字第號裁判意旨:「醫療行為具有相當專業性,醫病雙方在專業知識及證據掌握上並不對等者,應適用前開但書規定,衡量如由病患舉證有顯失公平之情形,減輕其舉證責任,以資衡平。若病患就醫療行為有診斷或治療錯誤之瑕疵存在,證明至使法院之心證度達到降低後之證明度,獲得該待證事實為真實之確信,即應認其盡到舉證責任。」
2.雷射近視手術併發圓錐角膜案
最高法院年度台上字第88號裁判意旨:「可見圓錐角膜確實可能係因雷射近視手術所致,而術前檢查亦可判斷病人是否適合施以雷射近視手術,是上訴人原可能以病歷證明其損害與被上訴人之醫療行為有因果關係,僅因該病歷未逾保存期限即遭被上訴人銷燬,致未能盡其舉證責任,依其情形,是否無民事訴訟法第條但書規定之適用?」嗣最高法院廢棄發回審理後,臺灣高等法院年度醫上更(一)字第1號判決即以「就醫療糾紛而言,一般人對醫學知識之認知遠不及醫師,況病歷資料由醫師記載,並由醫院保管(此參醫療法第67條第2項、第70條第1項規定自明),在醫師施行雷射近視手術之情形,關於術前檢查報告之解讀、醫師施行手術期間之狀況,病人自無從知悉,是在此種證據幾由醫師掌握,資訊顯不相當之情況,若由病人負擔醫師有無過失之舉證責任,對病人而言,自係顯失公平,揆諸上開說明,應減輕病人之舉證責任,始符公平。」而減輕病患關於醫師有無過失之舉證責任。
(二)「轉換」舉證責任
1.中耳炎手術案
最高法院年度台上字第號裁判意旨:「查本件患者係於年4月17日因中耳炎至被上訴人中港院區耳鼻喉科就診,由醫師A施行手術治療,於該日即成為植物人,此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而被上訴人於年6月8日所出具之患者診斷證明書僅記載:患者因患右側慢性中耳炎併膽脂瘤,於年4月17日在本院接受右側中耳顯微鏡手術(於全身麻醉之下),術後送麻醉恢復室觀察,在術後麻醉醫師觀察中,病人突然發生呼吸困難,麻醉醫師立即施予急救,急救後,病人成為植物人等語,並無關於醫師A如何為患者施行中耳炎顯微鏡手術、麻醉醫師又如何為患者實施全身麻醉之紀錄。如有此紀錄亦應由被上訴人保管。查患者在被麻醉及手術過程中,全程均在被上訴人醫護人員之照護中,竟成植物人狀態,倘無此醫療過程之紀錄,或被上訴人難以取得此項紀錄,而必欲令其負舉證責任是否有違公平原則,非無斟酌之餘地。」
2.椎體清除減壓案
最高法院年度台上字第號裁定意旨:「上訴人A於年2月7日為病患(已於同年月8日死亡,被上訴人為其繼承人)施行手術中失血高達c.c.,其出血量顯較文獻上所載出血量~c.c.(平均c.c.)高出甚多;衛生主管機關醫事審議委員會鑑定認為『手術中大量出血之原因,應為前位椎體清除、減壓術造成』、『手術時間長達十小時,失血達c.c.,應是引起血壓下降的原因之一,……本案死亡與手術應有關係』、『病人血壓下降可能另有原因。……造成休克及心肺衰竭,和病人之死亡有直接因果關聯』等。A就手術中狀況並未舉證證明病患自『16時15分至17時之間,血壓較低至70/30mmHg左右』引致失血量增加較快之原因,亦未證明手術時有何原因造成失血高達c.c.導致病患死亡,應有醫療過失,為原審認定之事實,且有醫審會年12月17日鑑定書可稽。另觀被上訴人已具狀質疑病患大量出血問題並指陳上訴人應就手術中大量出血及血壓下降之原因負舉證責任,原審受命法官於年7月7日行準備程序時諭知『依民事訴訟法第條但書,被上訴人(指本件上訴人)應舉證證明失血c.c.是(否)符合醫療常規』,程序上尚無不合。」
3.頭部外傷急診留觀案
最高法院年度台上字第號裁判意旨:「過失之醫療行為與病人之死亡間因果關係之存否,原則上雖應由被害人負舉證責任,惟苟醫師進行之醫療處置具有可歸責之重大瑕疪,導致相關醫療步驟過程及該瑕疵與病人所受損害間之因果關係,發生糾結而難以釐清之情事時,該因果關係無法解明之不利益,本於醫療專業不對等之原則,應歸由醫師負擔,依民事訴訟法第條但書之規定,即生舉證責任轉換(由醫師舉證證明其醫療過失與病人死亡間無因果關係)之效果。」
(三)實務見解之評析
實務界於民事訴訟法增設第條但書後,努力嘗試於個案中調整舉證責任之分配,以追求兩造當事人間之公平,實值敬佩。惟依前揭德國醫療訴訟之實務發展可知,為使醫病間符合訴訟上武器對等之要求,固應考慮以減輕或轉換病人之舉證責任,惟如欲發生舉證責任調整之結果,仍應具備前開「表見證明」、「重大醫療瑕疵」等特定類型為前提,縱認實務發展已採納前開重大醫療瑕疵理論為舉證責任轉換之依據,且承認在被吿違反病歷保存及記載義務時,亦得為舉證責任之調整,此在累積相當實務見解而形成一定共識後,固堪認誠為我國醫療訴訟得調整舉證責任之特定類型,惟仍有不少案件,係僅以平衡醫病雙方在專業知識及證據掌握上不對等,而在未說明符合特定類型之情形下,逕為舉證責任之減輕或轉換(如前述腎臟手術致十二指腸破裂案、本件健檢胸部X光誤判正常案之一審及更審後高院判決,詳後述),此或欠缺適用上之安定性,蓋絕大多數的醫療案件均存在上開兩造專業知識及證據掌握之不對等性,僅以此為調整舉證責任之理由,無疑使所有的醫療案件均符合調整舉證責任之前提,或有流於學者所指「基於直覺、感性(同情)等非理性因素或理由不足之論據,而任為舉證責任之調整」之虞,此外,在此情形下審理中應伴隨法官適當之闡明,使兩造得知「何構成要件」將為舉證責任之減輕、轉換,在減輕舉證責任之情形下,使他造有機會提出反證;在轉換舉證責任之情形下,使轉承擔舉證責任者得盡力為有利於己事實之舉證,否則,將更可能造成突襲性裁判之嚴重結果,而影響民眾對司法裁判之信賴。
再者,以舉證責任之調整而言,舉證責任之轉換無疑為最強烈之手段,故在適用上,減輕與轉換是否存在先、後之適用順序,亦未見最高法院表明。本文另就前揭最高法院裁判意旨於個案中所表示應「減輕」或「轉換」舉證責任之具體情形,說明意見如下:
1.針對病歷遭銷毀或記載缺漏,影響原告舉證之情形
民事訴訟法第之1條規定「當事人因妨礙他造使用,故意將證據滅失、隱匿或致礙難使用者,法院得審酌情形認他造關於該證據之主張或依該證據應證之事實為真實。」為舉證責任減輕之方式,屬民事訴訟法第條但書規定之「法律別有規定」之情形。依此,「雷射近視手術併發圓錐角膜案」、「中耳炎手術案病歷」遭醫院銷毀或病歷記載缺漏,以致原告難以進行舉證之情形,即可適用前開規定為舉證責任之減輕。倘病歷之銷毀或記載缺漏係被告過失所致,亦應得類推適用民事訴訟法第之1條規定,退步言,縱認立法者係刻意排除過失之證明妨礙,而不能認有法律漏洞並類推適用該條規定,亦可援用民事訴訟法第條但書規定,以減輕甚至轉換舉證責任,結果並無不同。
惟民事訴訟法第條但書規定「依其情形顯失公平」於病歷遭銷毀或記載缺漏之具體適用情形,如參酌德國法上「病歷記載義務違反」之舉證責任轉換要件,除醫師違反規定而漏未記載外,尤需該漏未記載足以顯示出有重大醫療瑕疵,蓋依德國聯邦最高法院見解,僅就醫師或醫院就與病人有關之醫療資訊,應記載而未記載,或雖記載而有遺漏而言,並非病人獨立據以請求賠償之理由,故原則上亦不當然導致因果關係舉證責任之轉換。僅在未記載或記載缺漏足以顯示有重大醫療瑕疵情事時,該未記載或記載缺漏才會發生舉證責任轉換之效果。以「雷射近視手術併發圓錐角膜案」、「中耳炎手術案病歷」而言,病歷之銷毀或缺漏,是否足以顯示出有重大醫療瑕疵,尚屬有疑,有無達到得適用民事訴訟法第條但書顯失公平而得以調整舉證責任分配程度之合理性,亦值斟酌。
另在「雷射近視手術併發圓錐角膜案」一案中,原告似於年12月24日至被告診所接受雷射手術,其後視力模糊時又於年11月2日為最後一次就診,於年7月30日請求調閱病歷而遭拒絕,依此前提事實觀之,被告就年12月24日之病歷,依醫療法第70條規定僅有保存7年之義務,則原告於年7月30日請求調閱病歷時,似已逾被告應負保存義務之期間,是否能將病歷銷毀致不能證明之不利益歸由被告承擔,殊值存疑。雖有學者認原告於年11月2日再次就診時,已生醫療糾紛,呈現有訴訟進行之可能性,而可期待被告就此證據方法具有重要性一情可得預見,應認被告負有保持證據之注意義務。惟醫療法第70條既已明文揭示病歷之最低保存期限,醫療院所對達最低保存期限之病歷可解免保存義務一事有合理信賴,是否適宜因患者事後再次到醫療院所爭執治療之結果,即將保存義務之期限延長或重新起算?被告就此銷毀病歷之不利益結果是否具有預見可能性?均屬有疑。遑論在一般民事訴訟中,消滅時效設立之旨即在督促權利人及早行使權利,理由之一即在於如此較易於舉證。本件姑不論原告之請求在實體法上是否罹於時效消滅,惟此倘為一般民事案件,原告本應承擔其過晚行使權利而難以舉證之不利益,應無在醫療訴訟中即為相異之處理並將此不利益歸由醫療院所承擔。
2.其餘認應減輕舉證責任之情形,除未建立特定類型為適用前提外,亦未說明「減輕」舉證責任係減輕至何程度
在腎臟手術致十二指腸破裂案中,最高法院年度台上字第號判決之發回意旨,認「醫病雙方在專業知識及證據掌握上並不對等者,應適用前開但書規定,衡量如由病患舉證有顯失公平之情形,減輕其舉證責任,以資衡平。」即有在未建立特定類型為適用前提下,僅以醫病雙方專業知識及證據掌握上不對等,即調整舉證責任之疑慮。臺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年度醫上更(一)字第2號判決即依發回意旨降低心證度,以(1)依證人A(開腹手術醫師)、B(病理科醫師)之證詞可知患者十二指腸破洞之可能原因,有手術、憩室發炎破裂、潰瘍等三種原因,而A之證詞已排除潰瘍原因,B之證詞則排除憩室原因,唯一可能原因即被吿實施手術所致。(2)長庚鑑定意見書之鑑定意見亦認患者之血紅素由14.8g/dl降至7.9g/dl,最有可能原因是腹腔內出血(腸道內或腸道外),若無吐血或解黑便或血便情事,則最有可能之原因,則是手術施行時之相關步驟所致。(3)依長庚鑑定意見及證人C(開腹手術醫師)之證詞,十二指腸第三部分與手術摘除左腎之解剖位置,為緊鄰關係,被吿實施手術確有可能造成十二指腸破洞等茲為論據,認患者十二指腸之破洞係被吿實施腹腔鏡左側腎臟根切除手術所致。惟綜合判決所援引之上開(1)、(2)、(3)理由是否已足使法院確信原告主張(即患者十二指腸破洞為被吿手術所致)為真實之心證程度?有無減輕原告舉證責任之必要?尚有存疑。
此外,最高法院年度台上字第號裁判意旨亦未藉此機會說明,民事訴訟之一般證明度為何?醫療訴訟減輕舉證責任後之證明度又為何?實甚為可惜。
3.認應轉換舉證責任之情形──瑕疵是否已屬重大?
最高法院年度台上字第號裁判意旨,似已採德國法上以重大瑕疵作為舉證責任轉換事由。惟德國法並不以該醫療瑕疵是否具有可歸責性為前提,與前開最高法院裁判意旨以「可歸責之重大瑕疵」而為因果關係舉證責任轉換,尚有不同。再者,德國法上所謂「重大瑕疵」,係指依照通常醫師所受之教育及醫學知識,該醫療瑕疵之發生,是不可理解的(該醫療瑕疵不該發生在醫師身上)。惟在該案中所涉及之醫療瑕疵:A、B醫師未依甲醫院急診作業手冊第四版規定,立即為滑倒頭部受撞擊之病患安排電腦斷層掃瞄檢查,留院觀察期間又未評定留院觀察級數,亦未每15~30分鐘觀察病患生命徵候,疏未從X光片發現顱骨骨折,因而未能發現患者顱內出血嚴重……。然前開醫療瑕疵縱認屬實,是否符合「依通常醫師所受之教育及醫學知識,該醫療瑕疵之發生係不可理解」此一要件,亦顯有疑義。是最高法院上開裁判意旨雖已將審判上舉證責任調整之實務見解往前推進一大步,惟實際之操作要件與內容,仍有待後續裁判於個案中表示意見以充實之。
代結語:健檢胸部X光誤判正常案之評析
本案中歷審裁判均以:患者健檢胸部X光片「顯示主動脈弓及主動脈肺動脈窗附近有疑似異常,上述之異常可能情形有:肺癌及縱膈腔腫瘤(如淋巴瘤、胸腺腫瘤、畸胎瘤等),並無法排除胸腺瘤初發病灶所造成之陰影」,A醫師為放射科專科醫師,其依據上開X光片判斷患者胸部為正常,並不正確,亦不符合當時臨床之醫療水準,咸認A醫師為有過失。
惟臺灣高等法院年度醫上字第6號判決(下稱更審前高院判決)針對因果關係部分,依據:一、患者於美國醫院之就診記錄,除罹患第四期之惡性胸腺瘤外,實際另有四個未含有癌細胞之淋巴結等多個病灶,而認健檢X光片之異常現象,並不當然證明原告斯時已罹患惡性胸腺瘤,亦有可能係美國醫院手術中發現之淋巴瘤,甚至可能僅係單純心臟附近血管鼓起所造成之陰影。二、馬偕醫院鑑定回函謂:依目前醫學知識及儀器設備,無從推斷患者於健檢時已罹患惡性胸腺瘤或其病程期數。三、惡性胸腺瘤醫學上並無特別說明是否循序由A演變為AB、B1、B2、B3及C之期型,或是自始至終為單一細胞型態,亦尚乏明確文獻得以證明罹患此疾病之某一類型者,因時間之延後加長而演變成為另一類型,基此,患者於健檢時已罹患胸腺瘤一節已難證明,且罹患特定期型之胸腺瘤在醫學上尚難分辨是否自其他期型演變而來,此外,該演變亦難認與時間之延後加長有關,是縱A醫師就健檢X光片有判讀錯誤,亦無法推認因此致患者延後治療而使惡性胸腺瘤病程進化為第四期之結果,是損害之發生與責任原因事實間尚不足認有相當因果關係(惟該判決認A醫師就健檢X光片判讀錯誤,致病患未能早期發現病因接受治療,受有肉體及精神上痛苦,並就此部分准病患慰撫金之請求)。
前開判決用心地調查並嚴謹地進行推論,實令人敬佩,推論的結果亦符合邏輯而甚具說服力,惟此裁判的結果正凸顯司法審理對於醫療訴訟「因果關係」認定之困境。蓋活體組織原具有不可預測性,醫學上對於疾病的治療或許有一定的常規,如有爭議亦可委託鑑定機關鑑定以供參考,惟對於疾病係如何演進及未來可能的發展,抑或如醫師為符合常規之醫療行為是否即足以避免損害結果之發生,均存有甚多未知的領域而難為必然之推論,是在醫療訴訟中,縱然針對醫師之醫療行為有注意義務違反一節,法院已獲確信之心證,然原告仍未必得以證明:如醫師履行注意義務,即得避免損害結果發生之因果關係,由此不難窺知因果關係誠為原告在醫療訴訟之舉證中相當困難的一個環節,相信本案中一審判決及更審後高院判決為因果關係舉證責任之調整,即係欲解決此困境並進而追求兩造間之公平。
本案最高法院於發回判決中,並未提及舉證責任之調整,僅以更審前高院判決認患者未舉證證明過失與損害間之因果關係,尚有疑義為發回之理由。更審後臺灣高等法院判決即就因果關係部分減經原告之舉證責任,並謂:依馬偕醫院第一次鑑定報告可知,健檢X光片雖不足以直接判定患者健檢當時已罹患惡性胸腺瘤,但X光片顯示患者當時的胸部確實有異常狀況(且無法排除為胸腺瘤初發病灶所造成之陰影),且倘A醫師為X光片檢查「不正常」之判定,患者必然會及早進一步檢查,不致遲至D醫院接受X光檢查始發現罹病,相較於腎臟手術致十二指腸破裂案關於舉證責任減輕之適用,本案中減輕原告舉證責任所發揮之作用應更為明顯,蓋如未調整患者之舉證責任,恐怕難以達到過失與損害間具因果關係之確信心證。最高法院嗣亦認同更審後高院判決關於減輕患者因果關係舉證責任之見解,駁回兩造之上訴而使本案確定。
綜上所述,醫療訴訟之審理,原告應就侵權及契約責任之權利發生要件事實負舉證責任,惟關於因果關係之舉證實際上是甚為困難的,不僅僅為兩造醫療知識及證據掌握之不對等,更在於疾病之演變或可能的因果歷程發展,在醫學的領域上多屬未知或難以證明,惟在審判實務上,因果關係舉證之重要性,往往是在被吿之過失經調查證據結果已獲確信心證之「後」,換言之,即被告之過失已被證明之情形下,故司法實務上為實現當事人間之公平,在協助原告進行因果關係之舉證上,做了不少努力與突破。惟在舉證責任調整之運用上,如「減輕」原告舉證責任即足使原告訴訟遂行上回歸與對造處於平等之地位,是否即無「轉換」舉證責任之必要?再者,醫療訴訟之本質原即存在專業知識及證據掌握之不對等性,以此為轉換或減輕舉證責任之唯一理由,是否符合民事訴訟法第條但書「顯失公平」之期待?均有賴學說及實務界提出進一步之見解,使民事訴訟法第條但書之操作更有標準可循。
此外,隨著薪資提升、預防醫學興起及「早期發現、早期治療」觀念的提倡,民眾多有定期健康檢查之意識,日後,類如「健檢胸部X光誤判正常案」即民眾罹病後,再回頭向健檢中心調取X光片或其他醫學影像資料作為治療參考,卻發現健檢中心影像資料已可見病灶此等醫療案件亦可能日益增加,惟誠如本件A、B醫師及甲醫院所為之答辯,健康檢查係為「健康人」所作的初步疾病篩檢,與一般因病痛而就診不同,易言之,一般就診所安排之各項檢查均係在疾病已經發生的前提下進行,與健檢係在疾病未發生之情形下進行,如乏受檢者之相關主訴,則欲自醫學影像中主動察覺出病灶,自較一般疾病就診所為之檢查有更高的難度,此差異性是否會影響司法實務上對注意義務之認定,亦值得後續觀察。
欢迎加入
月旦醫事法報告赞赏
转载请注明:http://www.shiningstudio.net/lrzey/4277.html
- 没有推荐文章
- 没有热点文章